很经典的一本书籍,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本书作品展英国探险家奥里尔·斯坦因和他在中国西部的考古探险活动,有较大的争议。他是尼雅遗址的发现者,也是敦煌藏经洞劫经的始作俑者,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但是,只要涉及新疆探险史,对斯坦因和他在中国西部的考古探险则不能避而不谈。斯坦因这个名字,常使中国人百感交集。一方面他在新疆和河西走廊发现了多个举世震惊的辉煌文物遗存,几乎完全重塑了世人对那个区域的历史文明看法;另一方面他又以一种帝国主义的作风,掠夺走大量文物。
斯坦因西域考古记预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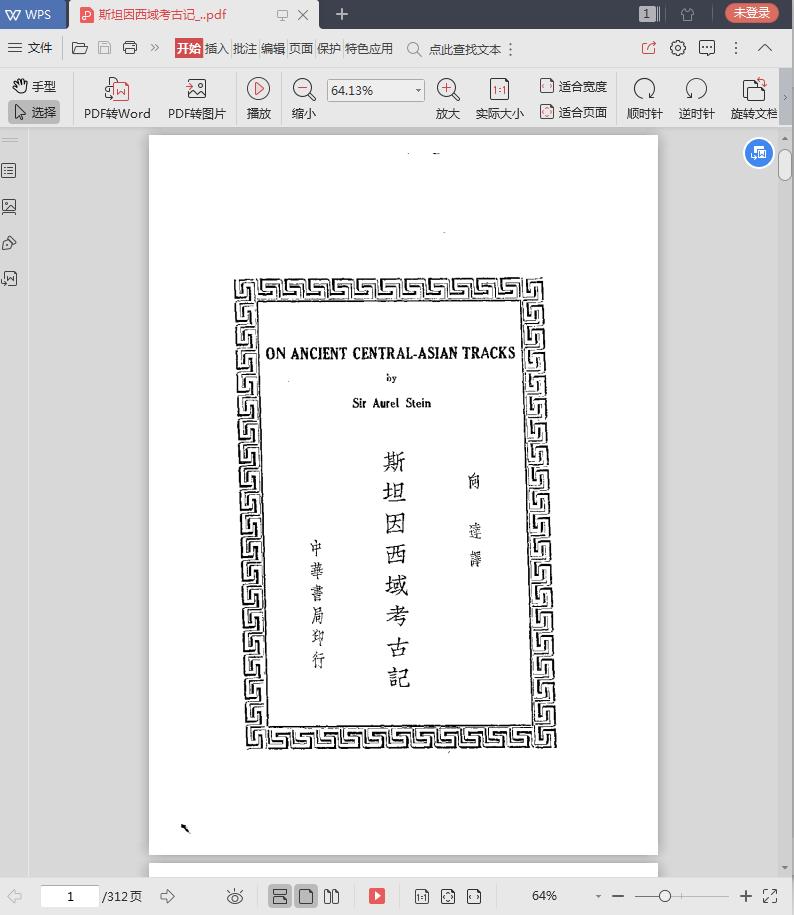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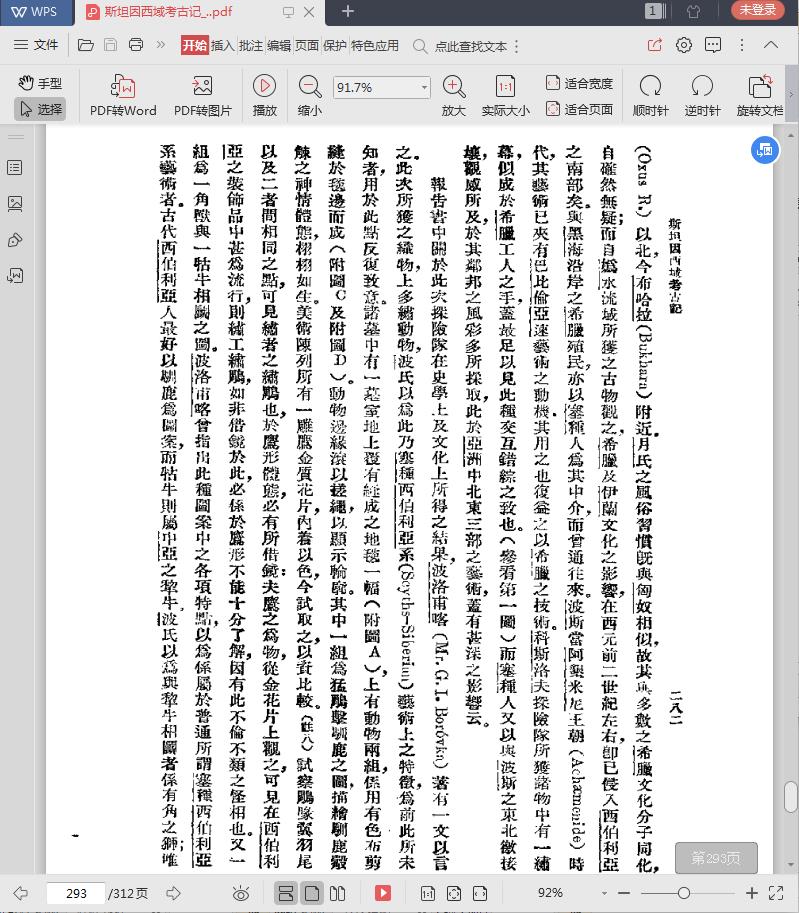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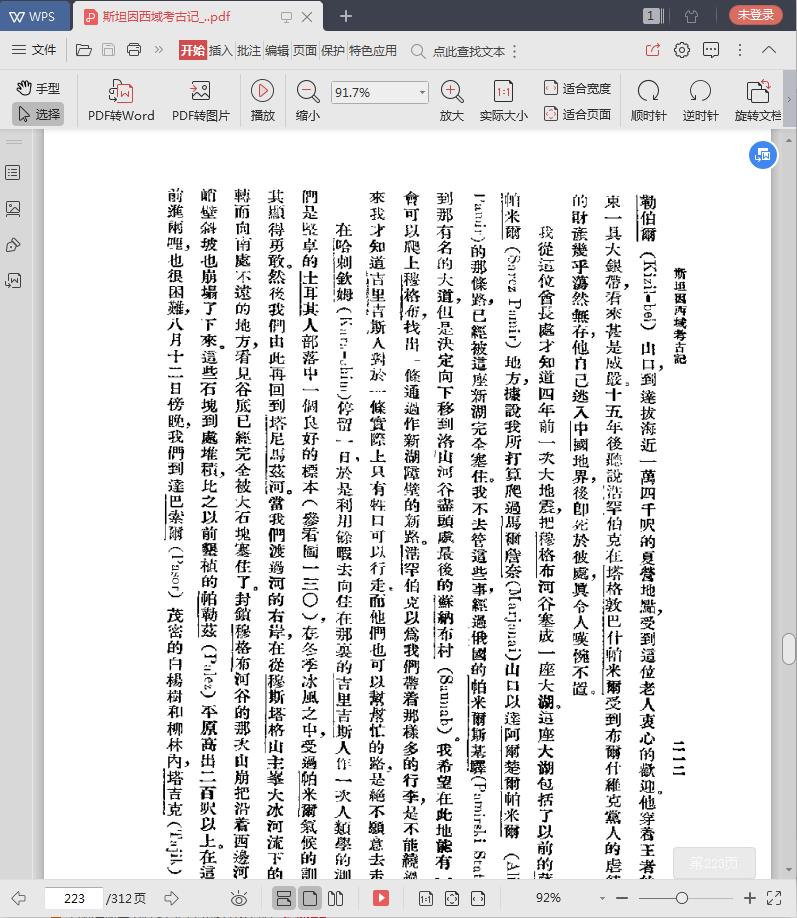
斯坦因西域考古记pdf目录
著者序
第一章 亚洲腹部的鸟瞰
第二章 中国之经营中亚以及各种文明的接触
第三章 越兴都库什以至帕米尔同昆仑山
第四章 在沙漠废址中的第一次发掘
第五章 尼雅废址所发现的东西
第六章 尼雅废址之再访和安得悦的遗物
第七章 磨朗的遗址
第八章 古楼兰的探险
第九章 循古道横渡干涸了的罗布泊
第十章 古代边境线的发现
第十一章 沿着古代中国长城发现的东西
第十二章 千佛洞石窟寺
第十三章 秘室中的发现
第十四章 千佛洞所得之佛教画
第十五章 南山山脉中的探险
第十六章 从额济纳河到天山
第十七章 吐鲁番遗迹的考察
第十八章 从库鲁克塔格山到疏勒
第十九章 从疏勒到阿尔楚尔帕米尔
第二十章 沿妫水上游纪行
第二十一章 从洛山到撒马尔干
附录
一 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略记
二 斯坦因黑水获古纪略
三 俄国科斯洛夫探险队外蒙考古发现纪略
四 十九世纪后半期西域探险略表
索引
斯坦因西域考古记读后感
斯坦因是较早在中国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的外国探险家,也是对新疆与中亚研究颇深的考古学家,与斯文赫定、伯锡和、格伦·威德尔、范莱考克、大谷光瑞、勒科克、橘瑞超俱参与了二十世纪初最中国西北地区的考察和掠夺,其一生著述颇丰,《西域考古记》为其中重要的一本,斯坦因考察了大量的考古遗址,其中不乏在茫茫沙漠中的大量探险活动,其行记至今无人复制,其对于新疆地区之考古意义重大,至今仍具有很大的价值,成为沿袭新疆考古者的必读之书。我曾两年在新疆进行考古发掘和调查活动,深知此书之重要性,但终于未曾仔细拜读,今日乃下决心仔细读一读,所读为1936年中华书局发行、向达翻译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竖排繁体电子版,后一半换成了201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横排简体纸质版,速度提高了两三倍。
全书分为二十一章,记录了作者三次在新疆考察(即作者所言之中亚、中国的土耳其斯坦)的情况,其中又轻松的游记,历史的叙述,也有严谨的考证,更多的是旅途的艰苦。
第一章为“亚洲腹部的鸟瞰”;介绍了新疆的地理环境、气候和道路情况。
第二章为“中国之经营中亚以及各种文明的接触”,介绍了中国历代王朝对西域的经略以及西域的历史。作者认为匈奴就是后来驰骋于欧洲的huns,今日则有两说,似乎认为这是两群人的更多。
第三章为:“越兴都库什以至帕米尔同昆仑山”,言继续了自己从帕米尔高原到和田的经历,其中穿插者人类学、语言学、地质学、考古学的调查。语之中可以看出来斯坦因对蒋师爷(蒋孝琬)这个助手十分满意。
第四章为:“在沙漠废址中的第一次发掘”,是作者在和田的发掘,作者到达被称为象牙房子的丹丹乌里克遗址,2009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丹丹乌里克遗址——中日共同考察研究报告》出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丛刊之一),报告认为“古代于阗王国的一座丝路重镇——唐代杰谢镇——丹丹乌里克遗址就掩埋在这片连绵起伏的黄沙之下[1]”,其为于阗军下属的一个镇,有护国寺一座。在这里,之前的斯文赫定曾经发生发掘过,斯坦因也雇佣了30名民工发掘了16日,详细地记录见于斯坦因《古代和田》[2]一书中,包括17座建筑遗址、一处圆形城墙遗址、一条古代运河、果园以及没有编号的房址,并绘制了较为详细的图,判断其为佛教圣地。遗址西南部为佛寺,有数座佛寺,有较多的雕像和壁画。斯坦因之后,但1996年考古学家才再次找到了丹丹乌里克遗址,之后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发现城墙遗址1处,建筑物遗址45处、篱笆遗址1处、炼炉、灶遗址1处,烧窑遗址11处,果园10处,总计70处。肯定了斯坦因判断其为佛教圣地的论断,CD8(策勒县丹丹乌里克遗址8号建筑遗址)即位文献记载的护国寺,绘制出了更加详细具体的平面图。在该报告末尾也提出了几个问题:如为什么没有发现佛塔,是因为没有发现还是宗教信仰的形式造成?为什么没有发现墓地,是因为距离居址比较远还是特殊的葬俗?至于具体的年代问题还有待于对陶器的断代研究。我根据书中的经纬度在谷歌地图上找到了这个区域,但是地图上什么也看不到,都是黄沙,看来这只有现场看才能看到了,这也算是卫片考古的局限性了。
第五章为尼雅废址所发现的东西。作者说到克里雅(于阗)之后受到村民的指引,这里“对于各种遗址即或是最小的,也都使用Kona-Shahr”,意即“古城”这一个名辞。”在尼雅遗址发掘过程中出土有大量的佉卢文简牍,这是当时极为难得的,其中一部分的封泥和封口上的绳子还在,能够清晰分辨其保险措施,十分难得,内容上,作者难以分辨,不过其字体较为随意,包括文书、练习和临时记事的东西。这种文字是印度西北部旁遮普的文字影响所致,当为印度西方之方言。
第六章为“尼雅废址之再访和安得悦的遗物”,在尼雅遗址发现的木牍的封泥上有赫拉克利斯(即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像,这或许与赫拉克勒斯信仰的东传有关,当时亚历山大东征之后希腊华时代的产物,邢义田先生的著作《画为心声》中有一篇《赫拉克利斯在东方——其形象在古代中亚、印度与中国造型艺术中的流播与变形》中有提出这样的观点[3],从亚历山大到之后的罗马、贵霜、斯基泰的君主很多都将自己的形象融入赫拉克里斯的信仰之种,让自己拥有大力神的装扮,这与中国云冈石窟的昙曜五窟和龙门石窟庐舍那大佛的显示对应类似。赫拉克里斯的形象随着亚历山大的希腊华时代到达中亚和印度,并与当地艺术结合,经过大夏传入印度,经过犍陀罗艺术的加工成为佛陀的护法,而其形象也一定程度上本土化,如希腊的大胡子变成了印度的小胡子,裸露的身体被厚重的衣褶覆盖,手中的棍棒也变成了金刚杵。这类金刚神的形象特出现在克孜尔石窟的壁画中,这类形象也出现在其附近的森木赛姆石窟,最迟在北周时期到达麦积山石窟,在这个过程中其面孔越来越东方化。进入中原之后其形象中的棍棒和狮虎帽形象融入到各类艺术题材之中,其本来的意义也消失了。
新疆的诸多古城遗址因为难以寻觅,故很多都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精绝古城、尼雅遗址、丹丹乌里克等地之遗址均为如此,而因为干燥的环境对遗物有较好的保存作用,其发现亦经常引起人们的惊叹,比如1995年中日联合考察团在尼雅遗址发现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的织锦就是最为传奇的文物,而大量埋在沙海里的简牍纸张文书、干尸及其随葬品更是引人瞩目,惊叹不已,为我们你了解古代社会提供了真实的一手资料。
第七章为“磨朗的遗址”,是1906年在若羌小沙漠之中调查与发掘。作者在磨朗遗址发现带有翅膀的天使,认为其形象来源怒希腊的天使,后经中亚传入中国。作者认为磨朗遗址可能是扜泥城的遗址,中国古书上所说的鄯善的古东城。
第八章为“古楼兰的探检”,与磨朗的遗址相去不远,发现大量的建筑遗址,其中又官署遗址,其中有大量的汉文公文,周围还有一些佉卢文和其他文字的资料,在一个汉文文书中有“建武十四年(330年)”的字样,此种记录当为长时间与中央政府失去联系所致,而这份文书是这里发现最晚的文书,作者当认为建武年号的时间为317-318(东晋元帝司马睿),故有此种想法。我有两个想法,第一,使用“建武”作为年号的中国古代帝王有七位,其中有十四年的为东汉光武帝刘秀和后赵武帝石虎,后者统治区域去此处较远,而前者到去世疆域也未曾也未曾到达西域,故皆不可能,作者根据整体判断其时间且认为其最晚,但未说明其具体原因;第二,这种中央王朝与边缘地区的长距离间隔产生的文化间隔也不少,如著名的龟兹左将军《刘平国碑》,其年代为“永寿四年(158年)”,为汉桓帝年号,但是永寿的年号只有三年,其时西域与中原交通不便,故尚不知年号变更之事。若羌出土的文书中常有减少口粮的命令,可见此处屯田之不能自给。此外,墓葬中发现的漆器和木耒也证明了中原文化对鄯善地区的影响。
此处沙漠中之建筑似乎长威红柳夹你墙所制,有防止风沙侵袭之作用,然更大的之城址当为夯土围城。作者根据文书考证出此处原名为Kroraina,认为“楼兰”或为音译[4]。根据玄奘《大唐西域记》记载:“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扜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户千 五百七十,口万四千一百,胜兵二千九百十二人。”林梅村先生认为楼兰迁徙到车尔臣河附近的泥城,更名为鄯善,而车尔臣(cherchen)就是鄯善的遗音[5]。其形制为采用汉代形制的方形结构,与这一地域最早的LE[6]城、西域长史所LA城和扜泥城都是仿照敦煌的汉式方城结构[7]。这也是判断汉城和本地城址的重要依据,林先生判断西域都护府之地望就以此项标准为重要论点,认为方形的阔纳克协海尔而不是圆形的卓尔库特更可能为西域都护府之治所乌垒城。
第九章为“循古道横渡干涸的罗布泊”,讲述作者1914年去罗布泊周围考察的情景,因为当局的变更而造成了一定阻碍,但是终于未能组织工作,最后还是在罗布沙漠中发现了一些遗物,也包括干尸,还有一些建筑遗址。作者在此处不禁感叹古代中国旅行家西行之困难和意志之坚定。
第十章为“古代边境线的发见”,是作者1907年从若羌到敦煌的见闻,自然可见多出遗址,其中也有居址和垃圾内的简牍,简牍格式多样,皆为随意的书写,也有练习的文字,但都经过多次书写和刮削,可见其时简牍之珍贵。
在谷歌地图上查看阳关和玉门关的位置,发现玉门关位于敦煌市(县级市,今属酒泉市,汉代敦煌、酒泉、武威、张掖为河西四郡)西北,阳关位于敦煌市西南,中间有一篇沙漠,三个点均位于沙漠边缘,古今道路必经之地。三处均为绿洲,敦煌市所在的位置绿洲面积最大,适合较多的人生活和驻军,其他两关均为小片绿洲,足以供给驻军,但是在古代不适合大量人员居住,且地理位置位于东西交通必经之地,故在这里设置关卡。这与南疆古今之城址多在沙漠边缘道理想同。概括其优点在于:第一为地理位置,沙漠边缘,东西来往的道路毕竟之地;第二为绿洲,第三为水源,玉门关周围有洋水海子,很多时候这和绿洲是相伴而生的。
第十一章为“沿着古代中国长城发现的东西”,汉代将塞(秦谓之长城)一直修到了龟兹,中间以每隔几十里(似乎是五十里)有一个烽燧,现在仍旧可见龟兹地区(今阿克苏地区库车县)的一些烽燧,如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克孜尔尕哈烽燧遗址,即丝绸之路-天山廊道的组成部分,就在著名的克孜尔尕哈石窟旁边耸立。作者在这些烽燧周围发现了一些汉文的竹简,婆罗米文字和其他文字的纸片,记录了此处烽燧的管理制度,并认为这些纸片是当时发现的最早的纸。
第十二章为“千佛洞石窟寺”,斯坦因1907年到达敦煌的石窟寺,当为莫高窟了,对其进行了考察并记录。听说了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事情之后就赶到了藏经洞,通过和尚之口得知了其大致信息,然而王道士虽然是一个贫苦的导师,但是对于保护佛经缺不遗余力,他数年来的化缘所得均投入到保护这些经卷之中,而斯坦因的利诱对其也并无作用,之后斯坦因所给的作为捐献给寺庙的钱也用于运输经卷到衙门这一活动中(不过很多被盗且佚失),这确值得尊敬。之后斯坦因得知其对玄奘之最为尊崇,乃自言为追随玄奘脚步而来,才得到了王道士的信任并获得了大量的珍贵经卷。其后国内对王道士(王圆箓)的批评实在是有点“难古人”的意思了,如余秋雨在他著名的《文化苦旅》中的一篇《道士塔》中就对其大加批判,这事也大部分人的心声,但王道士毕竟超脱不了自身的阶层和认识局限性,与其将这一切的罪过归罪于王道士,这个农民出身逃难至此的道士,毋宁将其归责于清政府和他的各层官僚,这是我们民族的痛苦回忆,正如看到《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8]》那样。
有些人说:幸亏外国人将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带走了,要不然一定毁于政治运动、宗教极端主义与愚昧无知,因而我们应该感谢他们,他们不是强盗而是救星。我对此观点不敢苟同,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盗,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外国,至于后来中国发生的变化与他们没有关系,他们也不可能出于拯救未来将要毁于政治运动中的文物的目的而将其运走。而在他们带走的这些文化瑰宝中,有的毁于战火,有的不知所踪,这或许并非其本意,但也令人遗憾。倘使这些文物运出之后全部在战争中炸毁了而中国却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这种观点还会有吗?只能说是一种历史的巧合,抑或误会吧。有些人说,走到哪里都是世界的嘛,文物放在哪里都一样,我对此观点亦不敢苟同。世界虽为一个整体,但是当今社会尚非大同社会,民族和国家仍然是重要的国际社会单元,如果大家都这么想本非不可,但只有一家这么想就会有问题,又有谁愿意将自己家的财产放在别人的家里而自己想要看看都很困难呢?当然,看到这些文物保存良好且能很好地发挥其作用,也算是失望中的一种自我安慰吧。
对这些“外国魔鬼”或曰“洋鬼子”的认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一开始称之为强盗,称之为“无耻的亡命之徒”,后渐有称之为探险家、考古学家者,甚至有些大加赞誉,这与社会背景有着深刻的关系。对于这些人我们自然不能一概肯定或否定之,对其学术上的重大建树则当在学术上肯定,其他方面亦当如此,而总体的评价则仁者见仁了。
石窟寺之开凿虽然有佛教之义理引到和选址的“山水形胜之地”的共同特征,但也有很多因地制宜的部分,其石窟内的艺术形式就与当地的地质条件尤其是石质有着密切的关系。凿新疆之石窟寺多为壁画,盖因为西域之山石刻修建石窟,但是不利于开凿造像,而开凿的石窟也未必权全是在石壁中开凿的,也有的是因地势垒砌而成,而造像比较少,且多为泥作。在河西地区如武威的天梯山石窟和中原北方地区的天水麦积山石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则多为佛教造像,盖与石块之材质适合开凿有关,又云冈石窟之砂岩较多,题造像略显更加粗犷,而龙门石窟多为石灰岩,质地坚硬、结构紧密且不易风化,适合造像艺术;至于在西域和河西东部之间的敦煌石窟则为砾岩和砂岩组合而成(砾岩多),结构不如其东部石窟砂石之稳定,故将石窟的开凿与泥塑、彩绘结合起来,造像多为木骨泥塑,这与中原一般寺庙的造像形式相同(如山西南禅寺、佛光寺)。
第十三章“秘室中的发见”,作者介绍了自己从王道士手中拿到大量的古本经卷和文书、绘画的过程,之后回国之后对其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其中包括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咸通九年的《金刚经》,这些丰富的文献为研究佛教、摩尼教和当时的各种文化情况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不过祖国的文化宝库,现在看来则多带有S、P的编号了。
第十四章为“千佛洞所得之佛教画”,本章中作者对其从莫高窟藏经洞所得的佛教绘画的介绍和研究,主要为绘画中的形象特征和性质。佛教之广泛传播与这些佛教绘画关系密切,其中经变画可谓为一种经文的转写形式,他不仅脱离了造像和壁画固定场所、大量资金要求的束缚,更带来了一种形象、直观的展现方式,将佛教的教义以故事、绘画的形式展现出来,便于最为广大的人民了解和信仰,走向大众是其繁荣的主要原因,伴随而其的是佛教翻译事业、造像事业和义理的发展,而其在宋代之后的衰落也正是因为“形胜于质”。
- PC官方版
- 安卓官方手机版
- IOS官方手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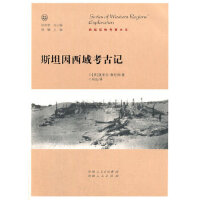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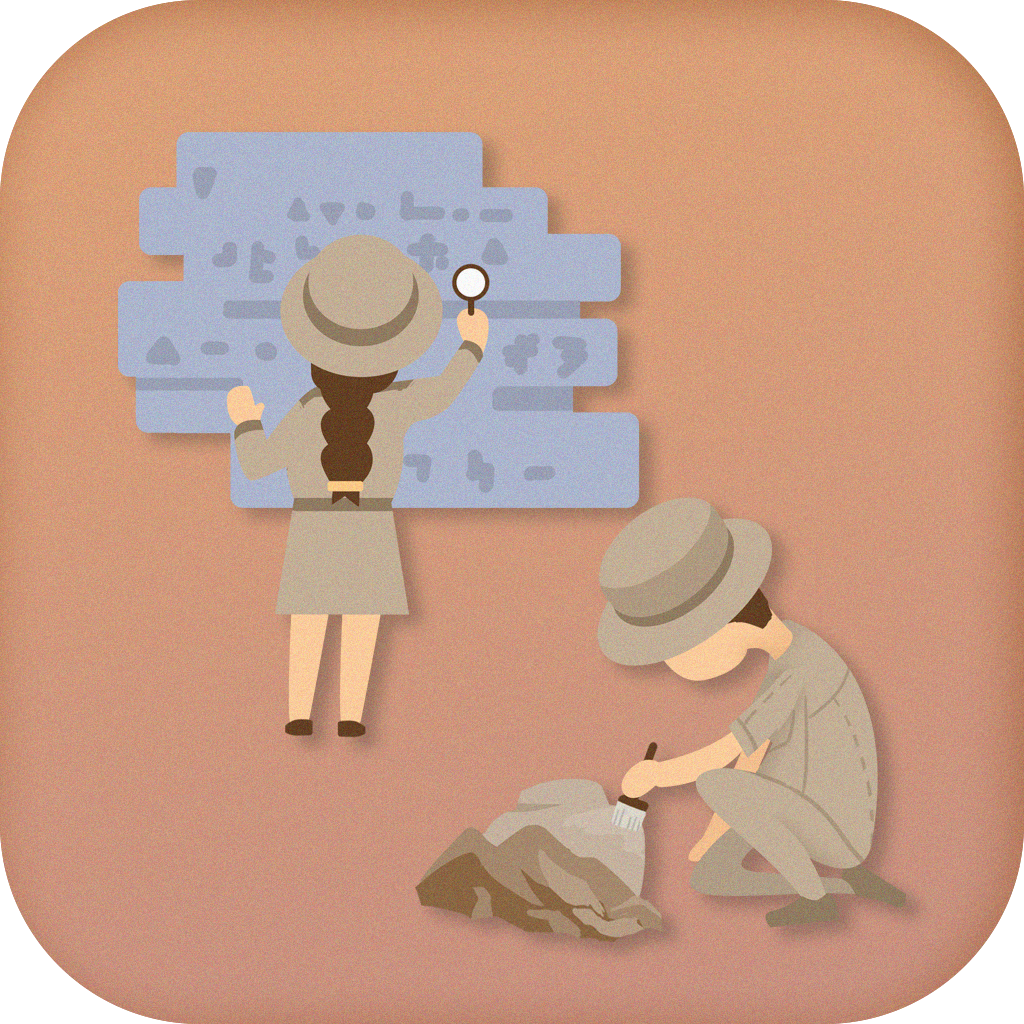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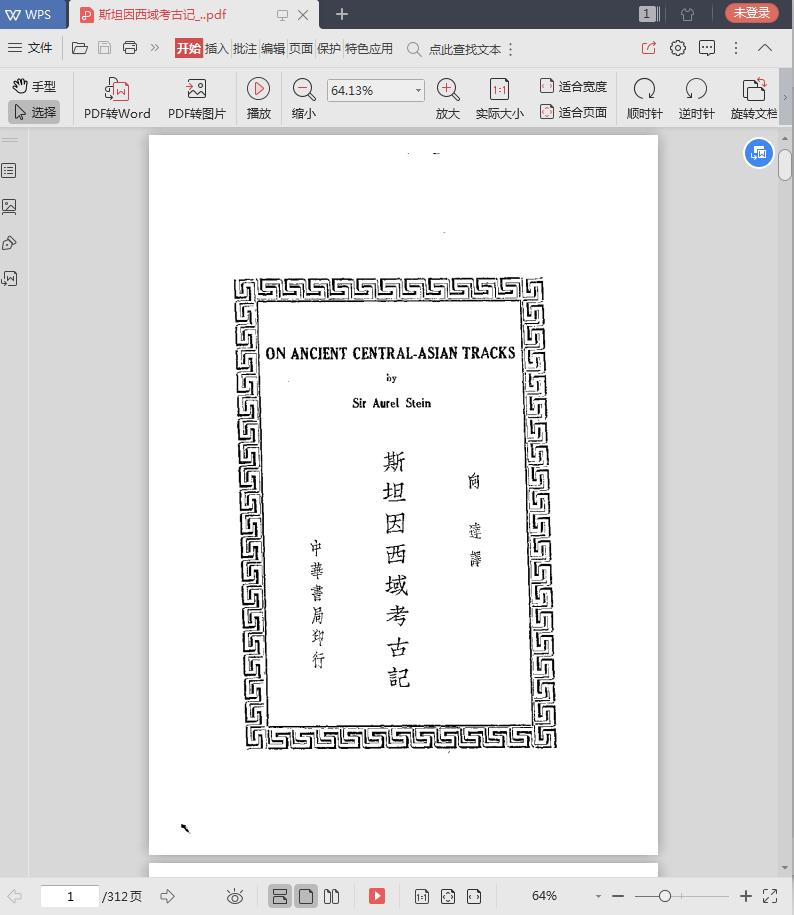

 苏轼诗集中华书局PDF免费下载
苏轼诗集中华书局PDF免费下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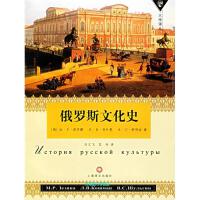 俄罗斯文化史pdf完整版
俄罗斯文化史pdf完整版
 警世通言电子版完整免费版
警世通言电子版完整免费版
 博弈论的诡计大全集(套装全4册)PDF免费版
博弈论的诡计大全集(套装全4册)PDF免费版
 羊皮卷大全集上下两册高清版
羊皮卷大全集上下两册高清版
 木工全书电子版全彩经典免费版
木工全书电子版全彩经典免费版
 帝鉴图说彩绘版旧版
帝鉴图说彩绘版旧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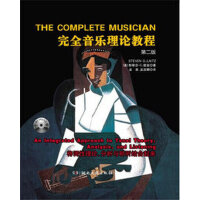 完全音乐理论教程第二版完整免费版
完全音乐理论教程第二版完整免费版
 尼伯龙根之歌完整版高清扫描版
尼伯龙根之歌完整版高清扫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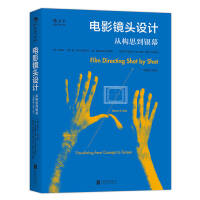 电影镜头设计:从构思到银幕高清完整版
电影镜头设计:从构思到银幕高清完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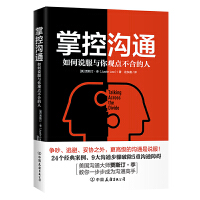 掌控沟通如何说服与你观点不合的人完整版
掌控沟通如何说服与你观点不合的人完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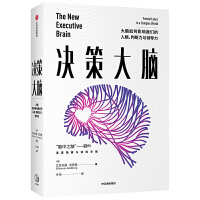 决策大脑pdf完整免费版
决策大脑pdf完整免费版
 色彩入门书籍13本pdf免费下载
色彩入门书籍13本pdf免费下载
 中国中医秘方大全上中下三册完整版
中国中医秘方大全上中下三册完整版
 图解说文解字画说汉字1000个汉字的故事pdf高清免费版
图解说文解字画说汉字1000个汉字的故事pdf高清免费版
 中国传世山水画高清版电子版
中国传世山水画高清版电子版
 世界名著200部PDF电子书
世界名著200部PDF电子书
 朝花夕拾全文免费阅读完整版
朝花夕拾全文免费阅读完整版
 天才在左疯子在右txt下载完整版
天才在左疯子在右txt下载完整版
 人性的弱点全集完整版
人性的弱点全集完整版
 gb4943.1-2011 信息技术设备安全pdf格式电子版下载
gb4943.1-2011 信息技术设备安全pdf格式电子版下载
 弹簧手册第二版pdf格式电子版下载
弹簧手册第二版pdf格式电子版下载
 化工工艺设计手册第四版(上下册)pdf格式高清完整版
化工工艺设计手册第四版(上下册)pdf格式高清完整版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完整版(孔飞力)pdf格式高清免费版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完整版(孔飞力)pdf格式高清免费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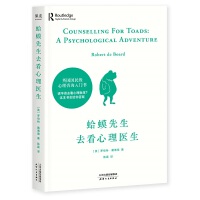 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电子书完整版
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电子书完整版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pdf免费版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pdf免费版 增广贤文全书电子完整版
增广贤文全书电子完整版 世界名著txt合集完整免费版
世界名著txt合集完整免费版